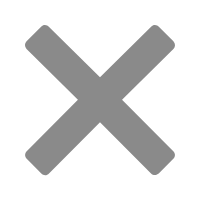-
八年恨海,用命换你帮我办后事
第一章
我和邹泽柏恨海情天整整八年。
又在所有人认定我们会一辈子纠缠的时候,和平分手。
再次见到邹泽柏,他因为新欢一句难听,把我妈留给我唯一一把吉他丢进河里。
我顺手把他砸成脑震荡。
“遗物又怎样,我故意丢下去的,只要你肯哭一哭,我赔一百把吉他给你。”
可那把吉他是唯一能支撑我活下去的东西。
我站在天桥上,对周围的劝阻充耳不闻。
把黑名单里的邹泽柏拉出来,释然开口。
“我哭不出来,能不能用一条命,换你帮我操办后事。”
1、
怀里抱着的吉他已经用了十年,拨动琴弦时偶尔会跑调。
我已经很久不出门见人了,如果不是今天有个认识的小姑娘求我在她的告白现场唱歌,我可能已经腐烂在家里。
一旁的宾客叽叽喳喳聊着趣事。
“邹家太子对女朋友真好,大街上亲自给她穿鞋。”
一旁手机屏幕亮的刺眼,听见这个名字我反射性抬眼去看,邹泽柏弯下从来挺直的脊背,给一个娇俏可爱的女生绑鞋带。
他脖子上有道狰狞明显的伤疤,谁也不知道那是我半夜按着他,拿刀割的。
我的锁骨上也少了一块肉,是被邹泽柏咬住活生生撕下来的,鲜血流了一地,他兴奋地不断舔舐。
告白进入尾声,我收好吉他准备回家。
一道甜糯得声音叫住我。
“一首歌一千,等会放烟花的时候你在后面伴奏。”
女人正是照片里邹泽柏系鞋带的女主角,我默不作声地准备离开。
才发现她给我挡得严严实实。
“泽柏很喜欢这首歌,他为我准备百万烟花,我也要给他一个惊喜,他一定会很开心吧!”
她兴致勃勃的对身旁的人说话,那人是邹泽柏的发小,王佑。
王佑脸色古怪,支支吾吾不敢看我,企图打消余伊白的念头。
“请支专业的乐队不好吗?”
他很明白,邹泽柏只要一遇见我,情绪就会失控,到时候还不知道闹出多大的事。
看着王佑调色盘一样的脸,我停下手里的动作,对着余伊白开口。
“可以,但是得加钱,一首歌一万。”
白白赚钱的机会不要白不要,我正担心我离开后,救助的流浪动物没人照顾,正好把这笔钱留给它们。
余伊白浅浅皱眉,从包里拿出一叠现金,丢进我身前的袋子里。
我抬手,王佑条件反射把人挡在身后,在他戒备的视线里我别过额前得头发,浅笑。
“老板大气。”
余伊白被拉的一个踉跄,不解的看王佑,突然眼睛一亮,高兴的向出现在河边的男人奔去,像一只快乐的蝴蝶。
王佑听见我的话十分不可置信,半响开口。
“玉姐,伊白和你不一样。”
我抱着琴调音,闻言挑眉。
“她柔弱、善良,连大声说话都不敢,就连有人提出过分的要求也不会拒绝。”
我听出他在内涵我刚刚一万块钱一首歌的话,淡淡道。
“所以呢?怕我发疯。”
“邹哥把所有关于你的东西都扔了,就连人,也不会找和你一样的,所有你以后别再打扰邹哥了。”
王佑嗓子有些紧,轻咳一声才继续说。
“也别伤害伊白。”
我目光淡淡望向远处的璧人,邹泽柏脸色没什么笑,握住余伊白的手不让她扑进怀里,似有所感,他迎着我的目光看来。
下一秒,他把女人拉进怀里,弯下腰,缠绵的吻难舍难分,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全是我熟悉的侵虐性。
他扶着双眸湿润的女人逐渐靠近,露出一如既往清润地笑。
“多年不见,装作不认识我?”
2、
余伊白视线在我和邹泽柏脸上转来转去,王佑赶紧出来打圆场。
“以前他们是一个学校的,勉强算校友。”
她恍然大悟,亲热的喊我姐姐。
“姐姐,听说泽柏大学时谈了段刻骨铭心的恋爱,你见过那个女人吗?”
岂止见过,现在就站在她面前,王佑捂住额头,邹泽柏从看见我开始,脸上的表情就没变过,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正在克制自己。
“问这件事干嘛?”
邹泽柏宠溺的点了点她鼻尖。
“一个不重要的疯子而已,说出她的名字别脏了你的耳朵。”
他以为这样会掀起我的怒火,可我已经很久感知不到情绪了,喜悦、愤怒、悲伤都没有,我的感情变成一顿虚无。
身后,几个人嘻嘻哈哈推来几千只玫瑰。
“邹哥,你要的1314朵玫瑰带来了。”
看见我,他们瞬间噤声,一个个瞪大眼睛,想看又不敢看的模样,有人踹了王佑一脚,让他给个解释。
他们的小动作很明显,全归咎于以前我和邹泽柏互相厮打的时候,他们也没少被波及,留下不少心理阴影。
我拿出歌单递出去,几人像炸毛的猫,齐齐向后倒退几步。
但我只是把歌单稳稳放进余伊白手中:
“点歌吧。”
邹泽柏一掌把歌单拍在地上,轻声细语和她说话:
“脏东西,别碰。”
“就听《ETERNALHEART》吧,里面有我想对你说的话。”
他余光挑衅,这首歌是我和他的定情曲,他买下全网版权,说这首歌这辈子都只能唱给他一个人听。
我轻轻稍动琴弦,因为不停地吃药,又不断呕吐,我的嗓子早被胃酸腐蚀,歌声略微沙哑。
副歌部分,邹泽柏掐住余伊白的腰,凶狠的落下一个吻,他喘息略微急促,不知道多少个日夜,这道呼吸也在我耳畔响起。
天空中巨大的烟花炸开,仿若星辰,我一遍遍唱着,直到眼前开始发黑,胃部也在不停痉挛,我知道自己发病了。
撑着膝盖,我有些艰难地喘息。
“不是想赚钱吗?我没喊停你不准停。”
邹泽柏用脚垫点点地上地吉他:
“唱一晚上,我给你一百万。”
余伊白有些担心:
“姐姐,你没事吧,如果累了可以回去休息,钱我会打给你。”
“装什么?”
邹泽柏嗤笑一声,毕竟我在他面前从来强硬,他从怀里掏出一叠美金,劈头盖脸砸我脸上,锋利的纸边在我脸颊划出浅浅血痕。
“泽柏,你这样有些过分了。”
我轻轻叹息,明明我不想动手的,抓起地上地点个板,我猛地拍向邹泽柏的太阳穴,力道太大,邹泽柏踉跄一步。
抓住他的脖子往后扯,怕他听不清楚,特意踹了他膝盖让他弯下双腿。
“我要回去了,听明白了吗?”
余伊白果然像王佑说的那样善良柔弱,她红着眼睛,连吼人的声音都不大。
“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再不放开泽柏我们报警了。”
半弯着腰的邹泽柏突然低低笑起来,手下皮肤滚烫,他呼吸粗重,明显情动的反应。
“寰玉,我给你脸了?”
他朋友终于反应过来,七手八脚把我拉开,也不敢动我,就挡在我面前,余伊白心疼的想看他的伤口,邹泽柏躲开,抓起我放在地上的吉他。
“十年了,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恋旧。”
我瞳孔紧缩,死寂的心因为他的动作重新跳动起来。
“放下它!你想怎么打回来都行。”
“这多无趣。”
邹泽柏摇头,吉他被他重重砸在地上,一脚一脚被踩成碎片,琴弦一根根绷断,发出清脆的声音,我被这声音刺激的浑身轻颤,突然想干呕。
我眼眶酸胀,但一滴泪都流不出来,只能一遍遍大喊:
“住手,邹泽柏,这是妈妈留给我唯一一件遗物!”
邹泽柏停下动作,恶劣地笑:
“我当然知道,对你没有意义,我砸它干嘛。”
“看着被毁坏的东西你一定很难受吧,放心,我很快让你看不见它。”
吉他从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咚被丢进奔腾的河里,无影无踪。
我目眦欲裂,蹲下身剧烈干呕起来,汗水鼻涕糊了一脸。
我知道,自己活不成了。
3、
许是我的样子实在狼狈,他的朋友散开。
“我可不敢碰她,寰玉的伤害值不是我能承受的。”
“以前不是一言不合就干吗?现在怎么这样...这样虚弱,不会是装的吧。”
我蜷缩在地上不停抽搐,妈妈的离去,家庭破碎,爱人反目,我已经扛了很久了,再也扛不动了。
王佑慌张的去找邹泽柏,他果然黑了脸,浑身散发着寒气,快步上前揪着我的领子把我拉起来。
“不过是一把吉他,至于反应这么大,以前也没见你这样。”
我强行忍住身体的颤抖,拍开他的手,啪啪两耳光甩在他脸上,瞬间浮起红色的指印。
“这是我妈唯一剩下的东西。”
邹泽柏顶顶腮帮,笑了。
“还想要遗物?隔天我帮你从你妈坟里再掏几件出来,想要多少都行,拿回去围成一圈,每天换一个抱着哭。”
我转身就走,邹泽柏没抓住我,跟着我走了两步。
“没意思,现在怎么变成一只软脚虾了。”
“不会是因为随时发疯被我抛弃了,现在看我找了个温柔的,也想装温柔点吧,可惜晚了,我不会再给你机会。”
他喋喋不休的话吵得我耳朵嗡嗡叫,最后他被咬着唇红着眼的余伊白拦住,才停下脚步。
我实在没时间了,和邹泽柏再纠缠下去会妨碍我做最后一件事。
我强撑着身体,把钱送去给救助点的女生,她不肯收,担忧的碰了碰我抽搐时咬坏的嘴唇。
“小玉,你又没吃药吗?”
我扭头固执地把钱塞进她荷包,脚下毛绒绒的小猫不断蹭着我的裤腿,痒痒的,可我笑不出来。
“药吃光了。”
“一个月的药一周就吃完了吗?你这样让我很担心。”
她身上的味道很温暖,和妈妈很像,也是我唯一愿意多聊两句的人。
也许是想给世界最后留下点什么,我没忍住倾诉的欲望。
“我又看见他了,还有他女朋友。”
“那首歌是独属于我和他的,但是他在歌里和别人接吻。”
“妈妈的吉他碎了,被丢进河里,我再也找不见了。”
我颠三倒四开口,想到一句说一句,语速混乱,可她听明白了,心疼的抱住我。
“会好的,我陪你一起去医院找医生。”
眼眶很酸胀,但还是哭不出来,我突然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想起架在邹泽柏脖子上的刀,很遗憾被他躲了过去,想起他从我锁骨咬下的一块肉。
“寰玉,别想着离开我,伯母的事就是给你的警告。”
我推开她,轻轻笑:
“我自己去就行,回见。”
最后摸了摸蹲在我腿弯里的大橘,我缓缓朝着天桥而去,胃部还在痉挛,我按压着肚子,河风把我的头发吹的乱飞,也吹干了浑身疼出的虚汗,让我冷的有些僵硬。
我拿出手机,从黑名单拉出邹泽柏的号码,才打开,他的消息源源不断发进来,嘲笑我因为一件遗物变得如此狼狈,企图刺激我的情绪。
我拨通他的电话,他几乎秒接。
“冷暴力是吧,不过一把破吉他,你既然这么喜欢,只要肯对着我哭一哭,我送一百把给你。”
风险些把我的声音吹散,我跨过栏杆,看着滚滚河水,轻轻开口。
“我哭不出来,吉他也不要了。”
“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我用一条命,换你帮我操办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