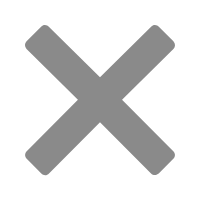-
第一百次剖心后,我不爱他了
第一章
我成年被拍卖那天,怀厌炸了整个拍卖场。
他捣毁本家实验室,推我坐上家主之位,自己却因心脏嵌着子弹,时时游走在生死边缘。“安宁,我要你清清白白站在阳光下,永远幸福。”
为确保手术万无一失救回他,我召集全球心脏权威,上百次剖开自己的胸膛给他们练手。
怀厌得知后,在病床上割腕自杀。
所有人抢救了三天三夜才留住他,可他闭着眼,再也不肯看我。
“安宁,我已经没用了,活着只是你的累赘,放弃我吧。”
那一刻我冲破心魔,再次拥住他。
我们像两只互相舔舐伤口的小兽,立下生死相依的誓言。
直到第一百次练手结束。
一个像百合般纯洁的女孩,拿着孕检单找上门:
“每次你刨心时,阿厌都在床上动情叫我的名字。一个被精心调教的性奴,凭什么霸占他?他甚至为了不和你上床,亲手往自己心脏开了一枪。”
我摩挲着孕七周的报告单,直接让人把她送进调教会场。
1、
我精心呵护五年的人就跪在我面前,面色苍白,垂着的眼里满是哀求。
“安宁,她只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你放过她。”
这是我第二次见他求人,第一次是因为实验台上将死的我,他匍匐在那人的脚边,低声下气的为我求来一丝生机,然后捣毁了整个实验室。
“剩下的药剂注射给我吧,再这样她会死的。”
第二次就是现在,他为藏了五年的小姑娘,在求我。
我捏紧掌心,指甲嵌入皮肉,才消散掉眼眶的热意。
“是她先来招惹我的。”
话音才落。
围栏里传来一声惨叫,一道带着倒刺的鞭子结结实实落在温晴云身上,她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挥鞭人淫笑着开口:
“继续脱!客人花钱买票可不是来看你装纯的。”
温晴云哆哆嗦嗦的护住自己最后一件衣服,哽咽开口:
“阿厌,我宁愿死也不想看见你求她。”
怀厌僵硬在原地,半响拉过我的手,摊开血肉模糊的掌心,轻轻吹气。
“她只是我一时兴起的玩物,不配你伤害自己,你放过她,我保证她以后都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等我取出心脏的子弹,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这次任由围栏里的人叫的再惨,怀厌眉头都没皱一下,温柔的规划者我们的未来。
可他颤抖的指尖出卖了他自己,我轻笑一声。
“五年一千八百二十五鞭,还剩一千八百鞭,只要她能挨完这些,我就放她离开。”
怀厌宠溺的在我手心中印下一吻:
“好。”
他揽住我的肩膀和我并肩站在一起,只是放在我肩头的手每打一鞭便捏紧一分,我的骨头似乎都要碎在他手里。
温晴云身上最后一件衣服已经被打碎,围栏周围的客人兴奋的喊叫:
“用力打!谁能把她骨头打出来,我加钱!”
更有客人疯狂的朝围栏里伸进手,企图抓住中央的温晴云按在自己的身下。
温晴云倔强的咬着下唇,蜷缩在地上无言的望着怀厌,突然她惊叫一声,双手捂住小腹。
“阿厌,我死没关系,但你救救无辜的孩子。”
浓稠的血液在她裸露的下半身蔓延开来,怀厌一掌把我推倒在地,还未愈合的心脏崩裂,鲜血沁出,打湿了我的衣衫。
我听见心脏在悲鸣着求救,疼痛席卷全身,可我仍旧固执的看着怀厌。
他扯过皮鞭,一鞭打断了挥鞭人的手,掏出枪开枪,正中眉心。
怀厌脱下外套,颤抖着裹住赤裸的温晴云,眼眶泛红:
“是我来晚了。”
他抱起温晴云,毫无停顿的越过我,我喊住他。
“怀厌。”
他顿住脚步,视线落在我染血的胸口,瞳孔一缩。
我几乎是屏住呼吸开口:
“放下她,和我去医院做心脏手术,然后我们结婚好吗?”
温晴云埋首在他怀里细细抽泣:
“阿厌,我肚子好疼,我们还不知道他是男孩还是女儿,会不会长得像你。”
“对不起。”
怀厌闭上眼,再次揽紧了怀里的人,头也不回的往外走去。
我失望的垂下眼,手指轻轻一动,整个会场被保镖围的水泄不通。
陈姨堵在门口,瞎了一只眼的脸上带着不诚心的恭敬:
“家主说了,一千八百二十五鞭,少一鞭都不能走。”
我接过钢鞭,强忍住剜心的疼,淡淡开口:
“我亲自动手,只需要一百鞭。”
怀厌死死盯住我,常年苍白的脸上都染上几丝薄红,我竟从他眼里看出蚀骨的恨意。
下一秒,他抬起手,黑洞洞的枪口正对我的眉心。
2、
怀厌为我举枪,指着过很多人的头。
实验室里给我注射超越我身体承受极限药物的研究人员,拍卖场里翻手为云的各方大佬,以及把我送进实验室的父亲。
我从一出手开始便是父亲的棋子,而我唯一的作用,便是成为他拉拢各方势力的性工具,月经初潮来的那天,也是我噩梦的开始。
数不清的针头扎进皮肉,非人的调教和刻在骨子里讨好他人的记忆,如果不是怀厌,我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怀厌是父亲最得意的武器,偏偏一个没心的人把他所有忠心都给了我。
他举着枪替我杀出一条血路,九死一生的把我送上家主的位置。
从此我不再是工具,而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
他胸口淌血,脸上却带笑。
“安宁,我要你清清白白的站在阳光下,永远幸福。”
但他永远为我而战的枪口,为了另一个女人,指向了我。
铺天盖地的悲哀将我淹没,我拿着鞭子的手却越发的稳,迎着他的视线,钢鞭狠狠落在两人身上。
“怀厌,有本事开枪。”
陈姨面沉如水想挡在我身前,被我推开。
他拿枪的手用力的泛白,手指却无论如何也扣不下扳机,终于他收回手,把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
“放我们离开。”
我刨心一百次都要救回的爱人,正在用他的命,换小姑娘的平安。
温晴云搂住他的脖子疯狂摇头,哽咽的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苏安宁,你以为当上家主就能改变你不过是性奴的事实,像你这样肮脏的人,怎么配站在阿厌身边...。”
她话还没落地,我猛地一钢鞭抽在她嘴上,一颗带血的门牙飞出,温晴云瞬间晕死过去。
“砰!”
震耳欲聋的枪声响起,怀厌对着自己大腿眼也不眨地开枪,鲜血在地上淌成一汪小泉,冒烟的枪口重新被移回他的太阳穴。
“如果晴云死在这里,我给她陪葬。”
当年他牵着我跑出实验室说的话还回荡在耳边。
“安宁,不管是生是死,我们都必须在一起,你愿意和我赌一赌吗?”
一瞬间,无力感席卷全身,钢鞭沉闷的砸在地上,我拂去眼角滚落的泪珠,踉跄着退后一步,哑着嗓子开口。
“放他们滚。”
怀厌一瘸一拐的快步离开,我望着他毫不犹豫的背影,心底最后一丝期待也彻底熄灭。
我闭上眼睛再也不看他一眼。
“告诉周家,我同意联姻。”
3、
我疲惫的回到家,只想好好睡一觉。
楼下却传来瓷器破碎的声音,我皱着眉站在楼梯口,陈姨正被怀厌掐住脖子撞在墙上。
见我出现,怀厌暗哑着嗓音开口:
“晴云流产大出血,整个A市的血库都被你用光了,你的血型刚好和她匹配。”
“安宁,这是你欠她的。”
我怒极反笑,冷哼一声:
“想要我的血,温晴云她够格吗?”
怀厌眼里闪过一丝厉色,陈姨被掐的喘不过气,双腿徒劳的蹬着。
我心口一窒,不敢想他会拿我视作母亲的陈姨来威胁我。
妈妈因为生我难产去世,是陈姨日夜不合眼守在我身边,才把早产儿的我拉扯长大,当年为了阻止我被送进实验室,被人活生生挖掉眼睛,丢进红灯区自生自灭。
我当上家主的第一件事,是拿枪端了整个红灯区,救回陈姨。
怀厌见我沉下的眉眼,笑起来:
“安宁,我发过誓永远不会伤害你。”
“但你也要为身边的人考虑。”
我终于点头,跟他去了医院。
冰冷的针头刺进我的皮肉,我整个人都开始控制不住的发抖,见我一瞬间苍白了的脸,怀厌眼里闪过不忍。
遮住我的眼睛,安抚的亲吻我的发丝。
“别怕,安宁,有我在。”
我仿佛又回到那间纯白的实验室,冰冷的液体,油腻的舌头在全身游走,挣不脱逃不开,唯一能带给我温暖的,只有怀厌遮住我眼睛的手。
那时他也说:
“别怕,安宁,我会救你。”
我条件反射的扑进他的怀里,用尽全力把自己蜷缩在他怀里,喃喃叫着他的名字:
“怀厌...怀厌。”
却丝毫没注意到怀厌僵硬的身体,本就没有痊愈的身体因为抽血越发困倦,我一时间忘了刚刚发生的所有事,依恋的开口:
“我们回家吧。”
下一秒我被重重从怀里推开,砸在墙上,疼得我闷哼一声。
怀厌惊喜的站起身:
“晴云醒了?”
他迫不及待地往病床走去,留下泪流满面的我。
刚刚被怀厌接触过的皮肤密密麻麻的传来蚀骨的痒意,我疯狂的抓挠皮肤,留下一道道血痕。
因为怀厌而治好的心理创伤,又因为他而复发。
甚至比以往所有时候都来势汹汹,我只觉得有上千只手游走在我皮肤上,恶心的我恨不得扒掉自己所有皮肉。
陈姨哭着把我搂进怀里,阻止我伤害自己。
病房里却传来悲怆的嘶吼:
“我的孩子!阿厌,我要她给我的孩子陪葬。”
温晴云跌跌撞撞的冲出来,举着一把水果刀胡乱的挥舞,眼见刀剑就要扎在陈姨身上,我摸向腰后的手枪,就要杀了她。
“不!”
怀厌目眦欲裂,比我更快的拿枪打中我的手腕,揽住温晴云的腰,任由她把刀插进他的肩膀,也不松开。
他用力抱住温晴云,不断向她做出承诺:
“我们还会有孩子的,晴云,你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直到温晴云情绪稳定下来,他才有时间抽空看我。
入眼的却是我无力下垂的手腕,怀厌眼角抽动一下,流露出无措和懊悔。
至此,怀厌对我所有的誓言,全部烟消云散。
陈姨捧着我的手腕,哀鸣:
“怎么会这样,怀厌!你怎么敢。”
我止住了陈姨所有话,踉跄的站起来,刨心的伤口再次崩裂,我却似乎感觉不到它的疼痛,轻轻开口。
“怀厌,你心脏那颗子弹,是你自己打进去的吗?”
“对!阿厌告诉过我,为了不碰你被改造的赢荡躯体,他宁愿往心脏上开枪。”
温晴云神色癫狂的接话。
“你竟然还妄图生阿厌的孩子,真是可笑,谁知道你会不会耐不住寂寞,跑出去厮混,最后怀个野种让阿厌接盘。”
“够了。”怀厌捂住她的嘴,视线却不敢看我。
他没有否认。
“哈哈..。”
我大笑起来,笑弯了腰,也笑出了泪。
原来如此,从一开始就是我的一厢情愿。
为了怀厌的上百次自愿刨心。
为了能拥抱怀厌,给他一个孩子,我在心理医生那里上万次的脱敏训练。
都是笑话!
我拂去眼角的泪,直起腰,在怀厌骤然缩紧的瞳孔里,对着心脏扣下扳机。
“怀厌,从此我们两不相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