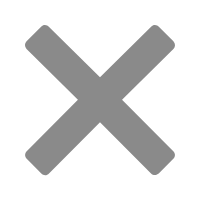-
送我去阎罗府后,他慌了
第一章
老公的养侄女又闯祸了。
为了保下她,老公想也不想把我送给A城只手遮天的阎罗,让我替她赎罪。
被老公绑上车的时候,我甚至生出果然如此的荒唐情绪。
艳门照、当小三,她惹出的所有祸事都被老公安在我头上。
我也曾哭过反抗过,但是都没用。
老公一句她是我的亲人,把我所有话堵在喉间,这次明知道我去赎罪九死一生,他也只是红了眼眶,亲吻我的额头。
“老婆,阮阮胆子小,你是她叔母,该和我一起保护她。”
见我没有一丝挣扎,主动上车,他松了一口气。
“我保证是最后一次,等你回来,我们去国外定居,到时候生个女儿。”
我木然的推开他的手,联系律师拟好离婚协议,订了出国机票。
1、
我蒙着眼睛不知道被带去了那里,比任修野这个名字更出名的是,他残忍的行事手段,得罪他的人,没一个还能健全的活着。
宋阮为了能攀上他,故意泼了他一身红酒,事后却哭着回来让宋时诏救她。
我站在空荡荡的房间,盘算着如果这次能活下来,就和宋时诏离婚,自己去国外定居,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次。
身后却突然覆上一具火热的躯体,灯光亮起,我才看清脚下踩着透明玻璃,玻璃下是各式各样的刑具。
“我本来打算让宋阮用她的皮来赔罪。”
炙热的唇细细密密落在我脖颈间,寒意从脚底窜起,我浑身汗毛直竖,身体僵硬的不像话,我以为自己早已能从容面对,但此刻我所有淡然都被扒皮两字击碎,害怕的眼角沁出泪来。
男人却突然笑起来,紧贴着我后背的胸膛震动的我心跳加快。
“但宋家送来了你,我改变想法了。”
“许向晚,好久不见。”
火热的手指在我身上四处挑逗,我心底一惊,喘息着想回头看他,却被蒙住了眼。
身体被侵入的那一刻,我呜咽着哭了出来,男人粗重的喘息声是掩饰不住的诧异。
我难堪的闭上眼,任谁也不会相信,结婚七年,宋时诏从来没碰过我。
新婚夜那天,宋阮在婚房外哭了一整晚,说被白天的鞭炮吓到了,要小叔陪她睡,宋时诏连一刻迟疑都没有,推开索吻的我开门离去。
此后每一次,我想和他亲热,宋阮总能准时出现,牙疼、旅游、逛街,数不清的理由把他从我身边叫走。
宋母本就不喜欢我,见我迟迟怀不上孕,更是加倍为难我,我没办法,甚至想到给宋时诏下药这一招。
那是第一次宋时诏对我露出厌恶的表情,他喘息着,却坚定的推开了我:
“我碰了你,阮阮会嫌弃我脏,别把自己当成一个荡妇。”
飞走的思绪被撞了回来,男人吻走我脸颊的泪珠,轻笑:
“别哭,我很喜欢。”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意识沉沉浮浮终于陷入黑暗,再睁眼,我正坐在车上,外面是宋家大宅。
推开门想下车,才发现腿软的一塌糊涂,踉跄着跌在地上,我仰头看着太阳,只觉得昨晚像一场梦,而我竟然活着从任修野那里出来了。
熟悉的脸占据我的视线,宋时诏面色阴沉,居高临下看着我。
“你竟然完好的回来了?”
不可置信的的语气刺痛了双耳,我愕然看着他,自嘲一笑,原来他巴不得我死在外面。
什么去国外定居,什么生个女儿,都是为了骗我心甘情愿为宋阮去送死的谎言。
尽管早就对宋时诏失望,我还是因为这句话乱了呼吸,为我坚守七年的婚姻感到不值得,也为年少时和他的两情相悦感到不值。
张了张口,我发现没什么能说的,沉默的从地上爬起来,宋时诏钳住我的胳膊,竟然带点关心的味道。
“他没对你做什么?”
我眼睫都没抬,果然宋时诏补上下一句话。
“你是不是逃跑了?你不去赎罪就只能是阮阮去,难道你想害死她?”
“阮阮还小,你忍心看她因为一个小错误被人折磨?和我走,我亲自带你去赎罪。”
他越说眉头皱的越紧,不由分说的就想拉我上车。
我脚步一个踉跄,挣脱了他的钳住,反手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小叔!”
带着哭腔的女声响起,我猛地被推在地上。
宋阮抖着手碰触他脸颊的红痕,眼泪像开闸的洪水,不停掉。
“你别求她,不就是赎罪吗?我自己去,就算任修野想要了我的命,我也无悔。”
她说的大义凌然,委屈的仿佛全世界都欠了她,我却听的只想笑。
“哈哈哈。”
我撑着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昨晚宋时诏绑我上车的时候,你不去。”
“你的私密照流传出去,宋时诏让我去认领照片,开新闻发布会受万人唾骂时,你不去。”
“你插足别人感情,正妻找上门时,把我踩在地上打时,你不去。”
我看着宋阮越来越难看的表情,只觉得七年来积累的所有不甘委屈都找到发泄口。
“现在我赎完罪了,你去又有什么用?继续攀附任修野吗?”
我拉开自己的衣领,浑身暧昧的青紫暴露在空气中,宋时诏瞳孔一缩,低吼。
“这是什么?”
我嗤笑一声,拂走额间的发丝,漫不经心的开口: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会活着回来吗?这就是原因。”
“我用自己的身体换了活下去的机会,从天黑到天亮,我讨好了他整整三晚,他才放过我。”
宋阮咬紧牙关,眼底是无论如何也藏不住的嫉妒和怨恨,我当然了解她在想什么。
“多谢你让我去赎罪,不然我一个有夫之妇,怎么可能爬的上只手遮天的任修野的床。”
“啪!”巴掌落在我脸上。
宋时诏打我的那只手颤抖,他额头青筋暴起,眼里闪过一丝悔恨和心疼。
“向晚,别说了,我会补偿你的。”
我冷笑一声,接过站在一旁律师手中的离婚协议,毫不犹豫的签下自己的名字,砸在宋时诏头上。
“不需要了,离婚吧,宋时诏。”
2、
宋时诏为我拉上衣服的手一顿,他看也不看地上的离婚协议,笃定地开口:
“向晚,别说气话。”
我低头看着被他踩在脚下的协议,自嘲一笑,他不会相信我会和他离婚。
年少的两情相许似乎还在眼前。
我和宋时诏从高中开始,便确认了心意,背着双方父母早恋。
宋母知道后勒令他和我分手,宋时诏倔强的在零下三十度的冬季跪了三天三夜,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永远不会和我分开。
我也以死相逼,才和宋时诏走到今天。
结婚时誓词我还记得,忠诚唯一,至死不渝。
但往事种种,在宋阮被爆出是假千金又被收为宋家养女时开始,像泡沫一样消散在我眼前,他看向宋阮的眼神藏着令人心惊肉跳的欲望。
一次次抛下我,面对我的质问是却神色坦荡,只说怜她身世坎坷,才事事以她为先。
就算犯下天大的错,宋时诏也只会用不懂事轻巧揭过,再把我推出去当挡箭牌,让宋阮能清清白白的地继续活着。
可我累了,我再也不想陪他们在爱而不得的戏码里,一直当被牺牲的角色。
宋时诏握住我的手,企图把我拉进他怀里。
“你别妄自菲薄,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不会因为这件事嫌弃你,昨晚发生的一切,都忘了吧。”
我猛地甩开他的手,只觉得被他碰过的地方让我恶心的想吐,我一眨不眨盯着他。
“签字吧,给彼此留点脸面。”
说完,我绕过两人往家里走去,打算收拾好行李,改签最早的机票离开。
到大门口时,才发现我所有东西都被丢在门口,我脚下踩着的,正是我和宋时诏的结婚照,大厅甚至挂上了我的黑白遗像。
我扭头看向心虚移开视线的宋时诏,深呼吸了一口气:
“宋时诏,如果我再晚两天回来,你是不是连我的死亡证明都开好了?”
宋阮挡在他面前,咬着下唇:
“别怪小叔,任修野的手段人尽皆知,你三天没回来,小叔怕你成为孤魂野鬼才好心给你布置灵堂。”
“死人的东西留在家里终归不好,我才收拾出来准备烧给你。”
“阮阮,别说了。”
宋时诏痛苦的闭上眼睛,隐忍着开口:
“是我的错,这些东西我都会重新买新的给你,别和阮阮置气。”
我看都不想看两人,蹲下身翻找奶奶传给我的玉镯,却怎么也找不到。
宋阮眼里闪过一丝得意,见我根本不搭理她,又咬紧了牙关。
“小叔,许姐姐被任修野接走的消息人尽皆知,她浑身青紫的回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发生了什么,还让她重新住进宋家,只怕会辱没宋家门楣。”
“还会说你...。”
宋时诏果然皱起了眉,刚刚捏过我的手不自觉在裤缝擦了擦,痛苦退去竟然是深深的嫌恶。
“我会在外面给你租个房子,这段时间,你先住外面吧。”
我翻找的动作一顿,缓缓站起身,死死盯住宋阮。
“我的玉镯哪里去了?”
宋阮表情一僵,又被我厉色下藏着的慌张取悦,动作怯懦的躲在宋时诏身后,表情挑衅。
“我觉得许姐姐总得留下点东西,就把玉镯捐给了慈善拍卖会,结果他们嫌弃玉镯材质不好,摔碎了。”
宋时诏果然把她护在身后,皱眉开口
“一个玉镯而已,想要我再给你买个。”
心脏猛地下坠,那是爱我的奶奶临终前留给我的唯一遗物,当时宋时诏甚至和我一起守着奶奶咽气,他知道这个玉镯有多重要。
我攥紧手心,心底的怒火越烧越旺,我抓起地上的剪刀,撞开宋时诏,把剪刀捅进宋阮的肚子。
玉镯破碎仿佛变成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所有的恨和悔都凝聚在剪刀头,一下又一下扎进下去。
我在宋阮惊恐的瞳仁里看见自己癫狂的脸。
“那就拿命来赔我的镯子。”
3、
“许向晚,你疯了!”
一股大力把我踹飞出去,我喷出一口鲜血,强撑着睁开眼看着宋时诏慌乱的抱起宋阮,面向我时充满杀意。
“阮阮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你生不如死。”
我本想就这样离开,宋时诏的保镖却拖着我跟着去了医院,我瘫倒在医院角落,五脏六腑疼的仿佛错位。
但我没吭一声,冷眼看着宋时诏在手术室门外焦急地踱步,从不信神佛的他甚至双手合十向上苍祈祷。
真是可笑,当初我替宋阮顶罪,被正妻一刀捅进腹部时,他也只淡淡嘱咐医生尽力医治,就转头安慰哭泣的宋阮,当天便带她去追极光。
医生浑身是血走出手术室,表情不太好:
“病人肾脏完全破碎,需要换新的肾。”
宋时诏猛地扭头,提着我的头发拖着我到医生脚边:
“是她害了阮阮,就用她的肾来换。”
我赤红着眼睛,哑声开口:
“宋阮害我切除了一个肾,现在你还要把我唯一的肾换给她,宋时诏,你想我死吗?”
宋时诏提着我头发的手越来越紧,他抢过医生手中的手术刀,抵在我的腹部:
“只要阮阮能变好,别的都不重要。”
霎那间我万念俱灰,锋利的手术刀在空中划过一道锐利的光,却在落下的前一秒被打断。
那晚在我耳边喘息了一整晚的声音响起,慵懒开口。
“你敢伤她一根头发,我就卸宋阮一个器官。”
我费力扭头,在看清任修野脸的一瞬间,瞳孔一缩,全身血液倒流。
任修野的声音不高,却像一道惊雷劈开了医院走廊里凝滞的空气。
他缓步走来,黑色风衣下摆在身后微微晃动,每一步都踏在人心跳的节拍上。
宋时诏举着手术刀的手僵在半空,脸色瞬间惨白。
他嘴唇哆嗦着,试图解释:
“任、任先生,这是我们的家事...许向晚她伤了阮阮,必须...”
“家事?”
任修野轻笑一声,那笑意却未达眼底,“在我的地盘上,动我碰过的人,你管这叫家事?”
话音未落,任修野突然抬腿,一脚狠狠踹在宋时诏腹部。
这一脚力道极大,宋时诏整个人向后飞出去几米远,重重撞在墙壁上,又软软滑落在地,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
任修野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走到我面前。他俯身,小心翼翼地避开我腹部的伤,将我打横抱起。这个动作与他周身凌厉的气场形成了奇异的反差。
“许向晚是什么人,我比你们清楚。”
任修野的声音冷得像冰,目光扫过瘫在地上的宋时诏,又若有似无地瞥了一眼手术室方向——透过门缝,能看见宋阮正惊恐地睁大眼睛望着这里。
“就算她真做错了什么,那也是她该做的。轮不到你们宋家这样践踏。”
这番话霸道得不讲道理,却让我眼眶一热。
七年来,我在宋家听够了“阮阮还小”、“你是叔母该让着她”、“这点委屈算什么”,这是第一次有人毫无条件地站在我这边。
任修野抱着我转身要走,却又停下脚步,侧头对挣扎着想爬起来的宋时诏丢下最后一句:
“记住,许向晚从现在起,和你们宋家再无瓜葛。再敢碰她一下,我不介意让宋氏从A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