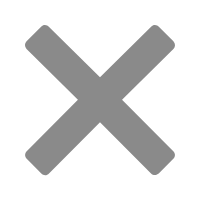-
带男友回村见家长后,全村人连夜磨刀
第一章
我总记得村口那抹洗不掉的血色。
当年,我爸赵老三带人把拐我的人贩子活活打死在那里。
多年后的我,走出闭塞的大山,学业有成,事业和爱情也迎来双丰收。
男友是警校出身,听说最近正在追一个拐卖的案子。
某一天,和男友闲聊时提起这段旧事,男友听完呆立半晌。
“晴晴,谁家人贩子去大山里拐卖孩童啊。”
“你有没有想过,被你爸打死的,才是不远万里来寻你的亲生父母?”
1
周正的话像一道惊雷,在我脑海炸响。
“不可能!”
我下意识地想要反驳。
“我爸那么疼我,为了我,他什么都愿意做!”
我爸赵老三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善人。
从小到大,家里哪怕穷得揭不开锅,只要我想吃肉,第二天桌上准有红烧肉。
我上大学那年,他把家里唯一的牛卖了,在村口哭得像个孩子。
哪有人贩子会对买来的孩子这么好?
周正看着我,苦笑着道歉:“抱歉,晴晴,是我职业病犯了。”
“最近这个案子太压抑,我看谁都像嫌疑人。”
他嘴上道着歉,但我看得分明。
他眼底那抹疑虑,并没有散去。
那一夜,我在出租屋里辗转难眠。
只要一闭上眼,村口那片早已渗入泥土的暗红色血迹,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记忆中憨厚老实的父亲,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此刻在我脑海里模糊不清。
他挥起锄头砸向那对男女的动作,一遍遍慢放,如幻灯片般播放。
“畜生!敢拐我的女儿!”
父亲当时的怒吼,曾是我心中最温暖的安全感。
现在,却成为我难以入眠的梦呓。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浑身都是冷汗。
凌晨三点,鬼使神差地,我爬起来翻箱倒柜,寻找家里的旧相册。
一本,两本,三本……
我一张张地翻过去。
有我五岁时扎着羊角辫,骑在父亲脖子上笑得开怀的。
有我十岁时得了三好学生奖状,父亲骄傲地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墙上。
有我十八岁考上大学,父亲在村口送我时,偷偷抹眼泪的背影。
可我翻遍了所有相册,都没有找到一张我三岁之前的照片。
一张都没有。
疑虑像野草一样在心里疯长,堵的我无法呼吸。
我必须回去。
我必须亲眼去验证那个可怕到让我窒息的猜想。
我抖着手订下最早一班回老家的高铁票。
因为手抖,支付密码输错了三次。
订好票,我给周正发了条微信。
“公司临时安排去邻市团建,三天后回来,别担心。”
我不敢告诉他真相。
我怕。
我怕有万一。
我怕连累他。
更怕如果猜想是真的,他是警察,我该如何面对他?
我独自一人,踏上了回家的路。
高铁转大巴,大巴转黑车。
路况越来越差,车身颠簸得厉害,窗外的景象从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逐渐变成了连绵不绝的贫瘠山脉。
一种从文明世界跌落回蛮荒的错位感油然而生。
我感觉自己不是在回家。
更像主动走进一只巨兽张开的血盆大口。
2
大巴车在尘土飞扬中停在了村口。
几个坐在村口大槐树下闲聊的老人看到我,立刻热情地招手。
“晴晴回来啦!越来越水灵了!”
“老三可真有福气,养出这么个金凤凰!”
我回过神,微笑着对他们一一回应。
穿过熟悉的土路,远远地,我看到了自家那个破旧的院子。
父亲赵老三正光着膀子,在院子里劈柴。
他背对着我,脊背因为常年劳作而微微佝偻,每一次挥斧都带着沉重的喘息。
听到脚步声,他回过头,看到是我,脸上的错愕只持续了一瞬。
随即,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绽放出巨大的惊喜。
“晴晴?你咋突然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他扔下斧头,在满是补丁的裤子上擦了擦手,快步走过来,想要接过我手里的包。
那熟悉的,带着烟草和汗水味的气息,瞬间包裹了我。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一路上所有的恐惧和猜疑,在看到他惊喜笑脸的那一刻,似乎都变得有些可笑。
“公司放假,我就想着回来看看你。”我随便找了个借口。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立刻忙活起来。
他抓起院子里养得最肥的那只老母鸡,手起刀落,动作麻利。
又从水缸里捞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鱼。
饭桌上,摆满了全是我爱吃的菜。
红烧鸡块,清蒸鱼,还有拿鸡蛋和肉末蒸的蛋羹。
“多吃点,在外面肯定吃不好,看你都瘦了。”
父亲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他自己的碗里却只有些咸菜。
温馨的饭菜香气驱散了心头的阴霾。
我狠狠扒拉着米饭,把那些可怕的念头都压了下去。
我一定是疯了,被周正那个乌鸦嘴给吓破了胆。
在这个贫瘠得只剩下石头的山村,是父亲用他弯下的腰,供我走出了大山。
我怎么能怀疑他?
哪怕这次请假全勤奖没了,能回来陪陪父亲也是值得的。
夜里,山村静得能听到虫鸣。
我起夜上厕所,路过堂屋。
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我发现堂屋正中央的神龛上,似乎多了个新东西。
以前那里只供奉着一个看不清面容的木头牌位。
现在,牌位前,一块红布上,郑重地摆着一串珠串。
那珠串在月光下泛着一种奇特的,油润的光泽,像是被人盘了很久。
我心里觉得有些好笑,父亲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迷信了?
出于好奇,我走过去拿出手机,对着那串珠子拍了张照片。
然后发给了周正。
配文调侃:“看,我爸新请的辟邪法器,叫‘嘎巴啦’,说是动物骨头做的,能镇宅,是不是很酷?”
周正几乎是秒回了视频通话。
接通后,屏幕那头的他脸色惨白,身后的背景是警局的宿舍。
“晴晴,你听我说,快回来,千万别声张。”
我被他这副样子吓了一跳,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怎么了?你别吓我。”
“那不是动物骨头!”周正的声音很着急,急促得让我害怕,“我的法医选修课是满分!我绝不会看错!”
“你仔细看那骨骼的纹理和密度!还有那种因为长期盘玩而形成的包浆色泽!”
“那是人骨!”
“而且看大小,是未成年人的指骨!”
“轰”的一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手机差点从我手里滑落。
人骨……
未成年人的指骨……
我僵住了,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身后,突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木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在寂静的深夜里格外刺耳。
父亲那幽幽的声音贴着我的耳背响起:
“晴晴,这么晚了,跟谁说话呢?”
3
那一瞬间,我全身的汗毛都起来了。
我僵硬地按下挂断键,转身。
父亲站在阴影里,半张脸隐没在黑暗中,眼神晦暗不明。
他手里还端着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茶缸。
“爸……”
我挤出一丝笑容。
“没……没谁。”
“跟同事吐槽公司加班呢。”
我不敢看他,一边说,一边把那串“嘎巴啦”手串迅速放回原位。
指尖触碰到那冰冷的珠子,像摸到了死人的手。
父亲没有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
我屏住呼吸,手心里全是冷汗。
时间仿佛凝固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就在我快要窒息的时候,他忽然咧嘴一笑。
“城里老板心都黑,不想干就不干了,爸养你。”
那一嘴常年抽烟熏黄的枯牙,在昏暗的灯光下格外森然。
“早点睡,别玩手机了。”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回房间的。
反锁房门的那一刻,我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冷汗瞬间浸透了衣背。
这一夜,我被噩梦死死缠住。
我梦见那串人骨“嘎巴啦”变成了一个个小小的骷髅头,围着我哭喊,向我索命。
我梦见村口那对被打死的“人贩子”,浑身是血地从地里爬出来,伸出干枯的手抓着我的脚踝,一遍遍地喊我“女儿”。
我还梦见周正被关在一个生锈的铁笼里,舌头被割掉了,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绝望地看着我。
惊醒时,枕头湿了一大片。
窗外,天刚蒙蒙亮,外面一片灰白。
意识逐渐回笼,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下去。
所有的恐惧和猜疑,都源于一个不确定答案的问题。
我到底是谁?
想要知道问题的答案,只要能拿到父亲的DNA样本去做一个亲子鉴定,一切谜团就都能解开。
科学的证据,是唯一能够终结这一切猜疑的武器。
我不愿意相信,那个养育了我二十多年,用他整个生命来爱我的父亲,会是一个恶魔。
只要证明我和父亲是亲生的,那所有的一切就都只是巧合,只是周正的职业病在作祟。
我必须拿到父亲的DNA样本。
头发,带毛囊的头发是最好的。
或者,是他的指甲,血液,甚至是没刷干净的牙刷。
我深吸一口气,内心做下了一个无比坚定的决定。
无论真相如何,我都要亲手揭开它。
哪怕结果会将我彻底摧毁,我也要知道,我究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
悄悄打开房门,我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
父亲的房间里传来了轻微的鼾声。
计划,在我的脑海中迅速成型。
4
天一亮,父亲就扛着锄头下地干活去了。
我像做贼一样溜进了他的卧室。
心跳如雷,震得耳膜嗡嗡作响。
父亲的房间还和我记忆中一样,简陋,但异常整洁。
床上的被褥叠得像豆腐块,棱角分明。
我扑到床上,掀开枕头,翻开被单,仔仔细细地寻找。
没有。
一根头发都没有。
干净得不合常理。
我不死心,又跑到床底下,把所有角落都看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
一个五十多岁,身体机能开始衰退的老人,怎么可能不掉头发?
我心里那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我又跑进卫生间。
卫生间同样干净得诡异。
洗漱台上一尘不染,毛巾挂得整整齐齐。
我拿起父亲的牙刷,上面连一丝牙膏沫都找不到。
我又趴在地上,仔细检查地漏的缝隙。
父亲昨天晚上明明洗过澡,可地漏里空空如也,别说头发,连根毛都没有。
一个独居、丧偶、年过半百的老男人,家里干净得像个无菌室。
这本身,就是最大的鬼故事。
绝望一点点攫住我的心脏。
我几乎要放弃了。
就在这时,我的目光扫到了客厅茶几上。
那里放着一把指甲钳。
指甲钳旁的垃圾桶里,还有几张揉成团的纸巾。
我扑过去,展开纸巾。
里面包着几片月牙形的指甲,边缘泛黄。
是父亲昨天洗完澡后剪过的指甲。
“爸,我去镇上买点女生用的东西!”
我给父亲发了条语音,没等他回复,就逃似地离开这个家。
一路狂奔,坐上了去镇上的大巴。
到了镇上,我直奔那家唯一的,小小的卫生院。
我气喘吁吁地冲进检验科,提交了样本和我的头发。
做完这一切,刚走出卫生院,我的手机就响了。
是周正。
“晴晴,你在哪?”他的声音里满是焦急。
“我……我在老家镇上。”我支吾着。
“你别怕,我已经在来找你的路上了,把你的位置发给我。”
听到他的声音,我一直紧绷的神经瞬间断裂,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傍晚,我在镇上唯一一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宾馆里见到了周正。
他风尘仆仆,眼下有淡淡的黑眼圈。
他一把将我拥入怀中,抱得很紧很紧。
我把这两天发生的一切,包括人骨手串和今天搜集样本的过程,都告诉了他。
周正听完,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晴晴,你有没有听说过,哪个镇上的卫生院,能做DNA亲子鉴定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是啊,DNA检测是高精尖的技术,怎么可能是一个偏远小镇的卫生院能做的?
周正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又要了一份样本,装进了专业的证物袋。
“我联系省城的检测机构,快递寄过去,这是最后的保底。”
寄快递时,周正特意用了假名和假地址,反侦察意识拉满。
做完这一切,我们刚回到宾馆,我的手机就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我接起来,是卫生院检验科打来的。
“喂,是赵晴吗?你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可以过来取了。”
我握着手机,愣在了原地。
周正看了看表,脸色更加难看。
“从你送样本到现在,连八个小时都不到。”
“一般的DNA检测,就算加急,最快也要24小时。”
“这里面有鬼。”
再次来到医院检验科。
昏暗的灯光下,那个戴着口罩的医生递来一个薄薄的信封。
我伸手去接。
指尖触碰到信封的瞬间,仿佛触电一般酥麻。
这一纸报告,判决的是生死,还是真相?
我的手指捏住信封边缘,准备撕开封条。
手在抖,怎么也停不下来。
我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撕开了信封的封条。
抽出那张薄薄的纸。
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从窗户射进来,像血一样,正好照在报告最下方的那个红色印章上。
我的呼吸,在看到结果的那一刻,瞬间停滞。
报告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
【根据DNA遗传标记分析结果,支持赵老三为赵晴的生物学父亲(父女概率99.99%)。】
我们面面相觑。
难道我冤枉爸爸了?
周正拿过那份报告。
他的眉头非但没有松开,反而锁得更紧了。
“不对!晴晴,你看这个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