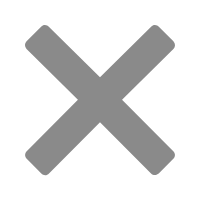-
宿管只收我的吹风机,我用她女儿的前途来偿还
第一章
高中三年,我最害怕就是冬天洗头。
头发还滴着水,我正要拿吹风机吹头。
宿管阿姨突然一把抢过吹风机,当众指着我骂:
“贱皮子,你是不是想整栋的人陪你下地狱?都说了寝室不准用吹风机,引起火灾了你负得了责吗?”
周围还拿着吹风机吹头的学生默默停下,注视着我这边的动静。
正值青春期敏感的我,有些无地自容,连忙小声解释:
“这只是600w的低功率吹风机,没有超过学校规定的800w。”
宿管阿姨还是一脸不耐烦地收走吹风机,并且通报处理。
自那以后,我只能顶着结冰的湿发去上课,因此落下终生偏头痛。
直到十二年后,我是负责教育局公务员的面试官。
一个格外优秀的女学生走进来。
看见她简历上的家庭信息栏上的“王秀梅”三个字,我笑了。
“抱歉,你没通过本次面试。”
1、
终面这天,李妍的履历十分漂亮,应答得体,无论是专业能力还是综合素质,都远超其他候选人。
身边的同事都暗暗点头,觉得这姑娘稳了,小声对我说:
“沈主任,恭喜哦,终于挑到称心如意的好兵了,这姑娘可以好好培养。”
我却没有应答,目光紧紧锁在家庭关系一栏的“母亲:王秀梅”处顿住。
脑袋突然疼得像被针扎,是偏头风又犯了。我抬眼看向女孩,她脸上还带着几分紧张的期待,眼神清澈。
我嘴角勾起一抹淡笑:
“很抱歉,你被淘汰了。”
李妍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为、为什么?我哪里做得不好,我可以学的!”
我没有解释,只是把简历推回给她,目光淡淡:
“你的政审过不了。”
李妍难以接受这个结果,下意识反驳:
“不可能!我家三代良民,都没做过任何违法犯罪的事,你凭什么张口造谣。”
李妍此时的气势完全不是刚才乖顺单纯的小年轻,而是有着她妈王秀梅咄咄逼人的影子。
还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我懒得理会她,转身留下一句:
“这你就要回去好好问问你妈了。”
“对了,近期我会给她寄去一份惊喜。”
回到车里,我连忙找了两颗药吞下,可偏头痛还是没有缓解。
十二年前,我才读高一。
是个敏感又内向的姑娘,父母离异,我跟着妈妈生活,日子过得拮据又小心翼翼。
自从王秀梅没收我的吹风机后,她就开始处处为难我。
她像是记恨上了我,专门盯着我找毛病。
寝室里其他同学用热水壶,她视而不见,可只要我拿出热水壶,哪怕只是烧一杯热水,她都会冲进来,一把夺过去,骂道:
“沈沐涵,又是你!不准用!你耳朵聋了吗?要是引起火灾,怎么办?”
“真不知好歹,像你这种听不懂人话的学生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握着空荡荡的手,小声解释:“阿姨,这只是600瓦的,规定是800瓦以下都可以用。”
“规定?”王秀梅冷笑,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
“规定是我说了算!我说不准用就是不准用!你耳朵塞驴毛了听不见?”
她把吹风机举过头顶,像展示战利品:
“都看看!这就是不守规矩的下场!”
然后她转向我,食指几乎戳到我鼻尖:“沈沐涵,我盯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单亲家庭出来的就是没教养,妈没教好你,我来教!”
“我没有。”我的声音在发抖。
“没有?”她提高嗓门,“上个月评助学金,你使了什么手段?嗯?我家李瑶成绩比你好,凭什么没评上?”
我愣住了。
直到这一刻,我才隐约明白她为何针对我。
“那、那是学校按条件评的。”我试图解释。
“放屁!”她打断我
“就是你这种穷酸相装可怜!我告诉你,以后你再用一次吹风机,我砸一次!用十次,我砸十次!我看你有多少钱糟蹋!”
她拿着我的吹风机,昂着头走出去,临到门口又回头。
“对了,今晚写一千字检讨,明天交到我办公室,不写就等着通报处分!”
门被摔上。
2、
宿舍里死一般寂静。
几秒后,对面床的刘小雨小声说:
“沐涵,你头发还湿着呢。”
我这才感觉到刺骨的冷。
水滴顺着发梢滑进衣领,冻得我打了个寒颤。
那一晚,我用毛巾擦到半夜,头发还是半湿。
第二天早上,它结了一层薄冰。
头痛就是从那天开始的。
自那以后,王秀梅的眼睛就像长在我身上。
有好几次,我参加晚自习竞赛辅导,回来时已经过了十点半的熄灯时间。
我站在寝室楼紧闭的玻璃门外,一遍遍按门铃,一遍遍喊:
“王阿姨,开开门……”
没有回应。
十二月的寒风像刀子,穿透我单薄的校服。
我蜷缩在墙角,看着自己呼出的白气在黑暗中消散。
手脚从刺痛到麻木,再到失去知觉。
三个小时后,接近凌晨两点,门才“咔哒”一声打开。
王秀梅裹着棉睡衣,手里拿着半个苹果,慢悠悠地啃了一口。
“哟,还知道回来啊?”她嚼着苹果,含糊不清地说。
“我还以为你在外面野死了呢。”
我浑身僵硬,几乎挪不动步子。
“磨蹭什么?不进来我就锁门了。”她不耐烦。
我踉跄着跨进门,一股浓郁的火锅香味从宿管室飘出来。
透过玻璃窗,我看到电磁炉上还冒着热气的小锅,桌上摆着肉片和蔬菜。
她跟着我的视线看了一眼,嗤笑:
“看什么看?我熬夜值班吃个宵夜不行?赶紧滚上去,别在这儿碍眼。”
走到楼梯拐角时,我听见她低声骂了句:
“活该冻死。”
那一晚,我发烧到三十九度。
第二天早上,头痛欲裂,像有锥子在太阳穴里凿。
但我还是去上课了。
因为王秀梅说过,无故缺课就要通报。
我不甘心。
看着其他同学照常用吹风机,甚至有人用明显超过800瓦的大功率吹风机,王秀梅却视而不见。
我又委屈又愤怒。
我开始省吃俭用。
早饭从菜包变成馒头,午饭只打一个素菜,晚饭有时干脆不吃。
三个月后,我终于攒够了钱,又买了一个400瓦的迷你吹风机。
这次我学聪明了。
我把吹风机藏在书包夹层里,只敢在澡堂人最多的时候,混在人群中,躲在最角落的插座前,飞快地吹几下。
第一次成功时,暖风烘着头皮的感觉,让我几乎哭出来。
但只用了三次。
那天晚上十点,我刚从澡堂出来,头发还湿漉漉地披着。
走到宿舍走廊时,王秀梅突然从宿管室冲出来,像早就埋伏好一样。
“沈沐涵!站住!”
我浑身一僵。
她一把夺过我的书包,粗鲁地翻开,精准地摸到了夹层。那
个小小的黄色吹风机被她掏出来,在灯光下像个罪证。
“能耐了啊?”她的脸在昏暗的走廊灯光下显得狰狞,“学会藏了?”
“阿姨,这个只有400瓦……”
“我管你多少瓦!”她突然暴怒,举起吹风机,狠狠砸向地面——
“砰!”
塑料外壳炸开,零件四溅。
一个小弹簧滚到我脚边。
“我是不是说过?”她逼近我,身上劣质香水混合着火锅味扑面而来。
“你是不是觉得我说话是放屁?啊?”
我盯着地上粉碎的吹风机,那是我省了三个月早饭钱换来的。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
“哭?你还有脸哭?”她指着我的鼻子,声音尖利得整层楼都能听见。
“你就是个不要脸的贱骨头!没爹教的东西!你妈是不是也这么不要脸,才被你爸甩了?”
3、
最后一句话像一把刀,捅穿了我所有的防线。
“不许说我妈!”我第一次吼出来。
王秀梅愣了一下,随即更加暴怒,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火辣辣的痛感炸开。我耳朵嗡嗡作响,听见她尖声骂:
“还敢顶嘴?!反了你了!明天叫家长!不叫就滚出宿舍!”
室友们看我的眼神从同情变成了恐惧。
刘小雨曾经偷偷把自己的吹风机借给我,让我在厕所隔间里快速吹干。
只借了两次,就被王秀梅发现了。
那天中午,我们正在午休,王秀梅带着两个学生会的干部,直接闯进我们寝室。
“都起来!”她踹了一脚门板。
我们惊慌地坐起来。
“谁借吹风机给沈沐涵的?”她扫视一圈,目光像毒蛇。
刘小雨脸色发白。
“不说是吧?”王秀梅冷笑,开始翻柜子。她似乎早就知道目标,径直走向刘小雨的柜子,从里面掏出一个粉色的吹风机。
“这是我妈给我买的。”刘小雨带着哭腔。
“你妈没教你不能助纣为虐吗?”王秀梅打断她,再次举起吹风机。
“不要!”刘小雨尖叫。
“砰!”
又一个吹风机变成碎片。
但这还没完。
王秀梅转向其他室友:
“你们的呢?都交出来!今天不交,我一个个柜子翻!翻到了全部处分!”
最终,我们寝室六个吹风机,全被砸碎在地板上。
五颜六色的碎片混在一起,像一场荒诞的祭典。
王秀梅踩着一地碎片,声音在寂静的寝室里回荡。
“都给我听好了!以后谁再敢借东西给沈沐涵,谁再敢帮她,一起通报!记过!档案上留一笔,我看你们以后考不考得上大学!”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看我:
“沈沐涵,你这种人,就是病毒。谁靠近你,谁倒霉。”
门关上后,寝室里久久无声。
刘小雨趴在床上哭了。
其他室友不敢看我,各自躺下,用被子蒙住头。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彻底被隔绝了。
我走投无路,去找班主任李国强。
在他的办公室,我磕磕巴巴地讲述这两个月发生的事。
被没收的吹风机、寒冬深夜被锁门外、当着全寝室的面被羞辱、室友被牵连……
李国强端着保温杯,慢悠悠地吹开茶叶,喝了一口。
“说完了?”他抬眼。
“老师,王阿姨她真的针对我,我可不可以换宿舍,或者……”
“沈沐涵。”他放下杯子,“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王阿姨只针对你,不针对别人?”
我愣住了。
“一个巴掌拍不响。”他靠在椅背上。
“你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不是你态度不好?是不是你不遵守规定?王阿姨工作很辛苦,管理一整栋楼,你要体谅。”
“可是规定是800瓦以下可以用,我买的只有400瓦…”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他不耐烦地挥手,“王阿姨说有安全隐患,那就是有,你要服从管理。”
我还想争辩,他突然问:
“你妈最近怎么样?”
“啊?”
“听说她打两份工?很辛苦吧。”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你更要懂事,别在学校惹是生非,让你妈操心。你要是被处分了,她得多难过?”
从办公室出来时,我浑身冰凉。
晚上,我听见刘小雨和另一个室友在阳台小声说话:
“真的,我亲耳听到的,王秀梅是李老师的亲妹妹。”
“怪不得……”
“嘘,小声点。”
我躺在床上,盯着上铺的床板,眼泪无声地流进枕头。
所有的路都堵死了。
4、
我给妈妈打电话。
“妈,能不能,再给我一点钱?”我握着公共电话的话筒,手指冻得发紫。
“又要钱?上周不是刚给你一百吗?”妈妈的声音疲惫而烦躁,“沐涵,妈妈真的很累,白天在厂里,晚上还要去超市理货,你能不能懂事一点?”
“我不是乱花,我需要……”
“需要什么?吃饭的钱不是给你了吗?你还想要什么?”
她打断我,“你是不是跟同学攀比?妈妈跟你说过多少次,我们家条件不好,你不要学那些坏习惯……”
“我没有攀比!”我哭着说,“我只是想买个吹风机,我头发…”
“吹风机?”她的声音陡然拔高。
“你心思不用在学习上,整天想这些?头发湿了不会擦干吗?妈妈小时候连热水都没有,不也过来了?你怎么这么娇气?”
“可是王阿姨她……”
“别找借口!”她彻底生气了。
“沈沐涵,妈妈拼死拼活供你上学,不是让你在学校享受的!你再这样,就别念了,回来打工!”
电话被挂断。
我握着忙音的话筒,站在寒风里,很久很久。
冬天最冷的那几天,气温降到零下。
洗完头后,我用毛巾拼命擦,擦到头皮发红发痛,头发还是半湿。
走出澡堂,寒风一吹,发梢立刻结起细小的冰碴。
它们贴在我的脖颈和脸颊上,像无数根冰冷的针。
头痛从此成了常态。
起初只是隐隐作痛,后来发展到只要一受凉,或者情绪激动,太阳穴就像被电钻贯穿,眼前发黑,恶心干呕。
我经常在课堂上突然抱住头,疼得蜷缩起来。
老师问起来,我只说感冒了。
我不敢说是冬天洗头冻的,不敢说是因为没有吹风机。
那听起来太荒谬,太矫情。
如果只是王秀梅,也许我还能忍。
但事情开始向更恶心的方向发展。
高二下学期,班里转来一个男生,叫陈皓。
成绩中等,但篮球打得好,人也长得干净。
不少女生喜欢他,包括王秀梅的小女儿李妍。
那时她还在读初中,但经常来高中部找她姐姐。
我不知道陈皓为什么注意到我。
也许是因为我总是独来独往,也许是因为我成绩还不错。
他开始给我传纸条,约我去图书馆,在我值日时留下来帮忙。
我拒绝了。
很明确地拒绝。
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我太清楚,像我这样的人,没有资格谈恋爱。
我要考大学,要离开这里,要赚钱养妈妈。
感情是奢侈品,我买不起。
但陈皓没放弃。
他坚持了两个月,直到有一天,王秀梅在食堂拦住了我。
“沈沐涵,”她抱着胳膊,上下打量我,“没看出来啊,挺有手段。”
我没说话,想绕过去。
她挪了一步,挡住我的路:“我警告你,离陈皓远点。人家家里什么条件,你什么条件?也不照照镜子,配吗?”
“我没…”
她冷笑。
“我都看见了,他给你递纸条,帮你值日。你这种单亲家庭出来的女孩,我见多了,就想着攀高枝改变命运是吧?我告诉你,做梦!”
她的声音很大,食堂里很多人都看过来。那些目光像针,扎得我浑身发疼。
“我没有。”我重复,声音在抖。
“还嘴硬?”王秀梅突然提高音量。
“大家都听好了!这个沈沐涵,看着挺老实,实际上心思多着呢!专门勾引男生,想靠男人翻身!她妈就是这么教她的!”
“你闭嘴!”我终于忍不住了,“不准说我妈!”
“我就说了,怎么着?”她逼近我,眼神恶毒,“你妈没本事,教出来的女儿也没本事,只会用下半身思考。”
5、
我没听她说完,转身跑了。
那天之后,谣言开始疯传。
版本越来越多,说我同时跟好几个男生暧昧,说我晚上去校外见社会青年,说我初中的时候就…
没有人来问我真假。
她们只需要一个谈资,一个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鄙视的对象。
而我,恰好符合所有条件:单亲、贫困、沉默、不合群。
完美靶子。
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
“沈沐涵,最近有些关于你的传言。”他推了推眼镜,眼神里有毫不掩饰的厌恶
“女孩子要自重,知道吗?你家庭情况特殊,更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而不是搞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想解释,想说这些都是谣言,想说我没有。
但他没给我机会。
“好了,你回去吧。”她摆摆手。
“以后注意点,别给班级抹黑。”
我走出办公室,站在走廊里。
同桌从我身边走过,假装没看见我。
前桌的女生和同伴窃窃私语,然后一起笑起来。
我站在那片橘红色的光里,突然觉得很累。
累到不想解释,不想争辩,甚至不想呼吸。
那天晚上,我照例去澡堂。
洗完出来,头发湿漉漉的。
走到宿舍楼下时,我看见王秀梅站在门口,正在跟几个女生说话。
她看见我,停了话头,上下打量我一番,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又去洗澡了?”她声音不大,但足够周围的人听见。
“洗这么勤,是要去见谁啊?”
那几个女生哄笑起来。
我没停步,径直从她身边走过。
上楼,回寝室,关门。
坐在床上,我用毛巾擦头发。
擦了很久,直到手臂酸得抬不起来。
头发还是湿的,但我没再擦。
就这样吧。
我躺下来,闭上眼睛。
湿着就湿着吧。
反正,已经不会更糟了。
头痛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
校医给我开止痛药,我吃到后来,需要两倍剂量才勉强有效。
高二下学期,我终于从室友那里得知了真相。
那天刘小雨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
“王秀梅的大女儿李瑶,跟你同届,在七班。去年助学金评选,她排在你后面一位,没评上。王秀梅去闹过,没用。所以她才恨你。”
我握着纸条,在厕所隔间里呆坐到上课铃响。
原来如此。
我所承受的一切,寒冬湿发、深夜锁门外、当众羞辱、头痛欲裂的折磨……
仅仅因为,我“抢”了她女儿的助学金。
而那份助学金,是我妈妈在工厂里弯腰十二个小时,是我一学期只吃最便宜的饭菜,是我所有努力换来的。
6、
高三那年冬天,头痛已经严重到影响学习。
我经常在晚自习时眼前发黑,不得不提前回宿舍。
但王秀梅不认校医开的证明,说我是装病逃避学习。
有一次,我疼得实在受不了,蹲在走廊里站不起来。
王秀梅走过来,用脚尖踢了踢我的小腿。
“装什么装?赶紧起来!别在这儿挡路。”
我抬头看她,视线模糊。
“看什么看?”她俯身,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们俩能听见的音量说。
“沈沐涵,我告诉你,你妈今天来学校了。”
我心脏一紧。
“她求我给你换个宿舍,求我别为难你。”王秀梅笑了,那种恶意的、畅快的笑?
“我告诉她,你女儿不守规矩,屡教不改,我也没办法。”
“你猜她说什么?她说对不起,是她没教好你。”
“啧啧,那么大年纪的人,在我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真是可怜。”
我浑身发抖,不知道是痛的,还是气的。
“不过嘛,”她直起身,声音恢复常态
“我看你也熬不了多久了。头痛是吧?疼死最好,省得我看着烦心。”
她哼着歌走了。
我瘫在地上,眼泪和冷汗混在一起。
那一刻,我恨她。
恨到骨头里。
高考那天,我顶着剧烈的头痛走进考场。
吞了三片止痛药,手心全是冷汗。
但我考得很好。
超常发挥,比平时模拟考高了四十分。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妈妈抱着我哭了。
她说:“沐涵,妈妈对不起你,妈妈不知道……”
她知道了一部分。
高三最后一个月,她偶然来学校,看到我湿着头发在寒风里走,才相信了我的话。
但太晚了。
偏头痛已经落下病根,成了终身的烙印。
大学四年,工作八年,十二年过去。
我成了教育局的公务员,一步步升到能负责重要岗位面试的位置。
我学会了控制情绪,学会了在头痛发作时面不改色。
我买了最好的吹风机,家里三个,办公室两个,车里还备着一个。
但我再也不会在冬天洗头了。
永远在白天洗,立刻吹到全干。
心理医生说,这是创伤后应激反应。
回到办公室,我锁上门,从最底层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
这次该王秀梅一家人偿还一切了!